为反跨性别法辩护的“专家”家庭手工业内幕

金·赫顿(Kim Hutton)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领导了一项为性别肯定提供护理的活动,当时她同意与一位持怀疑态度的人共进午餐。2013年10月,她在校园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遇到了该大学的儿科内分泌学家保罗·赫鲁兹(Paul Hruz)博士,希望如果她能分享自己为变性儿子寻找合适医疗服务的艰难经历,他会改变主意。
但赫鲁兹不听。
她刚坐下,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上帝对她儿子的安排”来。“我数不清他说过多少次,‘只要你读一下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关于性别的著作,你就会明白,’”她回忆说。
赫鲁兹明确表示,他将尽其所能阻止医学院开设新的性别诊所。当赫顿辩解说,如果没有得到肯定的治疗,跨性别儿童更有可能产生自杀念头时,他回答说,“有些孩子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受苦和死亡的。”
华盛顿大学不顾赫鲁兹的努力开办了性别诊所。但随着对跨性别者权利的攻击在全国范围内愈演愈烈,他开始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而且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角色。

赫鲁兹是为数不多但数量众多的专家证人之一,他们在全国各地作证,为面临法律挑战的反跨性别法律和政策辩护。他们从医学的边缘汲取灵感,目的是说服法官,性别确认护理在科学上是有争议的、不必要的和危险的。
大多数医生,像赫鲁兹一样,在与性别确认护理相关的领域行医——比如精神病学或内分泌学——但只治疗过少数患有性别焦虑症的青少年患者,如果有的话,也没有发表过相关的研究。一些人属于公开的反跨性别团体,并敦促州立法机构通过他们受雇捍卫的法律。
一些最著名的证人是由捍卫自由联盟(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招募的,这是一个保守的法律机构,其使命是实现一个由极右翼基督教价值观统治的国家。许多人和ADF一样,对LGBTQ+人群极度反感。
“他们是雇来的枪手,”LGBTQ+权利组织Lambda Legal的律师奥马尔·冈萨雷斯-帕甘(Omar Gonzalez-Pagan)说,他在几起案件中遇到了赫鲁兹和他的同伙。“他们不是真正的专家。他们是反对跨性别权利的人捏造出来的专家。”
不过,以每小时数百美元的价格,他们可以为学校的厕所限制和性别确认护理禁令增添一层科学严谨的色彩。
它们的影响越来越大。8月25日,密苏里州的一名法官暂时维持了该州对未成年人进行大多数性别确认治疗的四年禁令,他写道,“科学和医学证据相互矛盾,不明确。”
《赫芬顿邮报》查阅了数千页的法庭文件和数十个州供应商数据库,并提交了40多项公共记录请求,以全面了解他们日益增长的家庭手工业。调查显示,这些专家证人通常在短短几周的工作中就能拿到五位数的报酬。自2016年以来,州和地方政府在专家证词上花费了110多万美元,其中大部分都交给了六名证人。
一些州还高价聘请外部法律团队,另外花费660万美元。北卡罗来纳大学在卷入该州2016年的厕所禁令后,以每小时1075美元的价格聘请了保守派法律巨头众达律师事务所。
所有这些数字可能都低估了真实成本至少一半:在法庭上为反跨性别法辩护的30多个州和地方机构中,只有不到20个披露了它们的支出。
多年来,这些专家一直在努力建立自己在法庭上的可信度。法官们发现他们的证词“有偏见”、“不合逻辑”、“阴谋”或基于捏造,或者因为没有研究基础而完全抛弃他们的证词。美国十多个主要医学协会已经认可性别确认护理是医学上必要的,包括对青少年。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的政府几乎召集了所有著名的专家证人,起草和捍卫2022年该州禁止医疗补助覆盖过渡医疗的禁令。然而,用美国地区法官罗伯特·辛克尔的话来说,所有证人加在一起,“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治疗对经过适当筛选和治疗的患者造成了实质性的不良临床结果。”今年6月,辛克尔推翻了这一禁令。
但这是第一次,其他法院开始接受他们的论点。由于坚信攻击跨性别者是“政治上的赢家”,以共和党人为主的州议员在2023年提出了550多项新法案,攻击跨性别者的医疗保健和法律承认。因此,专家们不仅迎来了最忙碌的一年,而且还取得了几项关键的成功。
今年7月,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的一个小组允许田纳西州在法律挑战进行期间继续禁止性别确认护理。今年8月,美国第11巡回上诉法院恢复了阿拉巴马州对变性青少年使用青春期阻断剂和激素治疗的禁令。
法院运用与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相同的推理,裁定变性人护理不受宪法保护,各州只需要一些理由来规范它。专家证人是制造医学界存在分歧的印象的关键。“医疗和监管当局在使用激素疗法治疗性别焦虑症的问题上意见不一,”第六巡回法庭小组写道。
这些裁决增加了巡回法院之间出现分歧的可能性,也增加了最高法院最终处理性别确认护理问题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这些专家帮助阻止了全国数千名跨性别者获得必要的医疗护理。
“他们在浪费时间、精力和金钱,试图说服我和像我这样的人,我们不是我们所说的那样,我们也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高中生迪伦·勃兰特(Dylan Brandt)说,他是挑战阿肯色州在全国首个禁止为未成年变性人提供性别确认护理的主要原告。
“我很早就知道我是谁,现在我可以表达和展示我是谁,我感到非常高兴。人们如此努力,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阻止我,这很难。”
“请相信我和像我这样的人,我们不是我们所说的那样,我们也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他说。
除了赫鲁兹,核心专家小组还包括加拿大心理学家詹姆斯·康托尔(James Cantor);斯蒂芬·莱文(Stephen Levine)是一名临床精神病学家,当监狱面临提供性别肯定护理的压力时,通常会找他帮忙;前整形外科医生帕特里克·拉珀特(Patrick Lappert)曾表示,他认为性别确认手术“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恶魔”;内分泌学家迈克尔·莱德劳(Michael Laidlaw)敦促立法者将性别确认护理定为刑事犯罪;以及儿科内分泌学家、反lgbtq +美国儿科医师学会前会长昆汀·范·米特。
这群乌合之众并不是随机进入法庭的。拉珀特表示,对“愿意为反跨性别法辩护的人太少”感到沮丧的是,宗教右翼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捍卫自由联盟”(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于2017年在亚利桑那州举行了一次会议,以确定潜在的新成员。拉珀特后来在一份证词中描述了那次会议,赫鲁兹、范·米特和一位名叫安德烈·范·莫尔的加州家庭医生都参加了会议,并在不久之后成为了重要证人。几年后,ADF邀请康托尔参与他的第一个案件——另一名专家证人提起的诉讼,该证人声称他的大学因他的法庭工作而解雇了他。
ADF的招募工作立即得到了回报。大约在会议召开的同时,16岁的跨性别男孩阿什顿·惠特克(Ashton Whitaker)成为首批起诉学校厕所禁令的学生之一。诉讼称,他所在的高中是威斯康辛州基诺沙联合学区的一部分,该校的一名管理人员甚至建议他戴上亮绿色的腕带,这样老师就可以监控他上厕所的情况。
根据《赫芬顿邮报》获得的记录,基诺沙聘请的法律团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仔细研究过去的案例和医学期刊,以寻找潜在的专家证人——这项搜索只产生了几千美元的法律账单和一份似乎“可能支持”禁令的人的名单。后来,一位律师联系了捍卫自由联盟,基诺沙最终聘请了一位专家:赫鲁兹。
ADF在反对LGBTQ+权利的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证人名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该组织的创始人将其设想为“基督教法律军队”,每年有1.04亿美元的预算,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影响诉讼。《琼斯母亲》(Mother Jones)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性别问题上,它帮助组织了一群分散的反动和宗教右翼议员、律师和活动人士,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作小组,负责交易示范立法,协调公关活动,并对法案进行微调,以应对法律挑战。
一些专家证人是工作组的积极成员,例如Laidlaw。泄露给Mother Jones的电子邮件显示,他告诉立法者,性别确认手术是“等待被承认并写入法律的犯罪”。

基诺沙在审判和随后的上诉中败诉。此后,ADF开始与基诺沙的法律团队密切协调,试图在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在该地区最终选择和解之前,他们花了数周时间制定法律途径和法庭之友简报。
反对变性人权利的人在2010年代末和2020年代初输掉了他们早期的大部分法律斗争——基诺沙只是其中之一。但是新的专家骨干并不缺少工作。尽管他们今天的首要任务是捍卫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性别确认护理的禁令——这些禁令针对的是青春期阻断剂和激素治疗——但核心专家小组已经捍卫了各种各样的反变性政策,从学校体育和浴室禁令,到调查支持孩子变性的父母虐待儿童的命令,再到禁止对成年人进行性别确认护理的禁令。
最多产的是加拿大心理学家康托尔(Cantor),他总共见证了24起案件,仅今年就有11起。紧随其后的是莱文(Levine)和赫鲁兹(Hruz)。莱文曾在至少12起反跨性别法的挑战中担任证人,也是唯一一位在治疗跨性别者方面有丰富经验的辩护证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每小时的收费在200美元到650美元之间——这是庭审专家证人的标准价格——用于撰写报告、作证和出庭作证,以及旅行。康托尔在接受采访时说,当他亲自出庭作证而不是通过视频作证时,他通常会多赚1万美元,因为他要出差,还要在法庭上等待。
记录显示,在勃兰特诉拉特利奇案中,迪伦·勃兰特是原告,阿肯色州向赫鲁兹、拉珀特和莱文每人支付了4万多美元。(“是的,我觉得薪水不错,但远没有你的信息显示的那么高,”莱文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
作证的社会学家马克·雷格纳斯(Mark Regnerus)将57062美元收入囊中。Regnerus是一名资深的专家证人,他之前曾作证说,同性伴侣的孩子在为同性婚姻禁令辩护时处于不利地位。法庭记录显示,赫鲁兹在向阿肯色州提交专家报告几个月后,又向北卡罗来纳州出售了一份“几乎相同”的报告。
Lambda Legal的高级律师卡尔·查尔斯(Carl Charles)说:“这不是一份一小时200、300、400美元的工作。”但他推测,很少有人愿意这么做,因为“这些法案对年轻人和他们的家人造成了真正的伤害,我认为医生们对此非常重视。”

加拿大心理学家康托尔并不认同像ADF这样的团体的宗教使命。他把自己能够在禁止10岁变性女孩参加女子垒球队或阻止成年人在政府文件上更正性别等案件中作证归功于“内心的火神”,这是最近的两个例子。
他说:“当我第一次开始与这些团体联系时,我必须和自己进行一次漫长而艰难的对话。”“我最终决定,社会怎么做不是我说了算。这取决于社会。”
尽管他比其他任何专家都为更多涉及跨性别儿童的政策辩护,但康托尔从未为跨性别儿童或青少年提供过咨询。他也从未进行过涉及跨性别者的原创研究。他的专长是性反常:不正常的性欲,比如恋童癖。他在法庭上承认,性别焦虑症——当一个人不认同自己出生时的性别时所感到的痛苦——并不是一种性反常。
2022年,在西弗吉尼亚州禁止跨性别女孩参加学校体育运动的一项证词中,康托尔想不起任何阻止青春期发育的药物的名字:“哦,我不能告诉你它们的名字,而是它们的作用,”他说。“我一直不擅长记名字,”康托尔告诉我。“这些药物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名字。”
康托尔认为,由于缺乏直接经验,他能够冷静地评价这个领域。
他说:“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类比是,如果你想知道算命是否有效,你不可能仅仅通过问算命师就知道。”
去年夏天,他为印第安纳州禁止跨性别女孩参加女子运动的禁令辩护,他的证词表明,他不相信跨性别青少年是真正的跨性别者,而主要是同性恋、年轻、“错误地将自己的情绪”误认为是性别焦虑,或者是有自恋癖(autogynephilia)。自恋癖是一种异类理论,认为一些跨性别女性仅仅是被自己是女人的想法所激发。
他在我们的采访中说,“这只是一种不同的现象,只是表面上看起来相似”。
他还认为,研究“一致地,甚至一致地”发现,大多数认为自己是变性人的年轻人在几年后就不再这么做了。但他引用的许多资料来源并不是针对跨性别儿童的研究:在多个例子中,研究人员并没有区分那些始终坚持认为自己是跨性别儿童的孩子和那些只是以与异性相关的方式行事的孩子。有几项研究是几十年前的,研究主题是“娘娘腔男孩综合症”。
最近的研究发现,由于社会压力和缺乏父母支持等原因,变性儿童的变性率非常低。
康托尔说,他为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臭名昭著的指示辩护,该指示要求调查那些接受性别确认护理的儿童虐待儿童的父母。在阿拉巴马州禁止为未成年人提供性别确认护理的案件中,他赚了52400美元。由于康托尔缺乏对待跨性别青年的经验,该案的法官、特朗普任命的莱尔斯·c·伯克(Liles C. Burke)裁定,康托尔的证词“分量很小”,并阻止了禁令生效。尽管如此,自2022年5月的裁决以来,仍有十几个州要求他担任专家证人。在我们谈话几天后,第11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伯克的裁决。
“人们心中的问题是,他这么说只是为了钱吗?”康托尔在我们的采访中说。“如果我对文献的评价是相反的,我就会站在另一边。这不会有什么不同。所以我得到报酬是件好事,对吧?”

莱文拒绝接受采访,因为他是至少一个正在进行的案件的专家证人。(《赫芬顿邮报》联系了这篇报道中提到的所有专家,尽管多次尝试,但都未能联系上拉珀特。)在回答具体问题时,莱文写道:“你的问题说明了信息是如何被曲解的(原文如此)或完全错误的。就像通常包含真理核心的错觉一样,正是对现实的扭曲使错觉成为可能。”
1997年,他主持了今天被称为WPATH的组织的一个委员会,该组织制定了治疗性别焦虑症的最佳做法。然而,在他看来,WPATH对跨性别倡导过于敏感之后,他切断了与WPATH的联系。
在他开始以专家证人的身份为反跨性别法辩护之前,莱文曾为试图阻止跨性别囚犯进行社会转变或接受性别确认护理的监狱提供专家证词,这些监狱通常出于成本原因而反对。
在这个角色中,莱文还质疑跨性别者是否真的是跨性别者,或者他们的性别焦虑实际上是一种越轨欲望的表达,或者是童年时期未解决的问题,比如“过度共生”的母性。对于一名跨性别囚犯,他写道,她的“跨性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与她自恋的性格、苛刻的性格联系在一起。”

范·米特(Van Meter)是美国儿科医师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s,简称ACPeds)的前主席,他至少在六个病例中出现过。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和ACPeds最初的创始人一样,他对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感到失望,并寻求另一个选择,因为美国儿科学会不会认同“完整的已婚家庭”比同性父母和单身母亲更优越。
范·米特见过极少数患有性别焦虑症的青少年患者,但他说,他认为“100%”的病例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家庭环境。“离婚可能是所有这些案例中最常见的线索,”他说。他将这些患者推荐给抑郁和焦虑的咨询,相信这将解决他们的性别不安——这种方法源于同性恋转化疗法,研究表明它与自杀企图的风险增加有关。
范米特说,允许青少年变性“基本上是毁了他们的生活”,所以他一有机会就迫使他们放弃这个想法。对他现在的一个病人,“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你永远是一个生理上的女性。”
“你有一群人说他们存在,而他们说的是,‘不,你不存在。你不是真的,你有病,’”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儿科教授米歇尔·福斯特(Michelle force)说,她是专门从事性别确认护理的临床医生。“让我们明确一点:这些是欺负孩子的成年人。”

迪伦·勃兰特决定在阿肯色州提交案件的那几天不在法庭上,但他的母亲乔安娜·勃兰特却在。对她来说最艰难的时刻是,反对同性父母的社会学家雷格纳斯(Regnerus)把跨性别青少年的自杀风险降到最低,说研究人员“记录了相当少的真正完成自杀的人”。
他说:“如果我们把自杀和实际的自杀——完成的自杀——区分开来,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更狭隘的故事得到证实。”
乔安娜想起了迪伦,泪水刺痛了她。
她回忆说:“我害怕自己会大哭起来,所以我起身离开了。”“你怎么能到这里来,用这种方式谈论这些你从未说过话、对他们一无所知的人呢?”通过肯定的护理挽救了实际生命,而州政府方面没有人关心这一点。”
赫顿永远不会忘记她和赫兹的午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赫鲁兹作为一名专家发展了他的副业,她开始在一些和他一样的审判中作证。
在2017年的一起案件中,赫鲁兹为圣约翰县学区的厕所禁令辩护,她在佛罗里达州中部的一家法院回忆起赫鲁兹是如何说她的孩子可能“生来就会受苦和死亡”的。今年夏天,她飞往塔拉哈西,再次与赫鲁兹对决,这次是针对该州的医疗补助禁令。(她只报销了旅费。)
她的目标是让法庭了解他的真实动机。“我知道他现在在法庭上把他的整个陈述都包装成基于科学的,但这并不是保罗·赫鲁兹的动力,”赫顿说。“这是宗教。”
赫鲁兹并不是唯一一个有宗教动机的专家。

拉珀特以前是整形外科医生,现在是阿拉巴马州一个名为勇气(Courage)的天主教组织的牧师。根据该组织网站的介绍,该组织为“有同性吸引力的男女提供贞洁生活的建议”。在2018年的一次题为“变性手术与基督教人类学”的演讲中,他说手头的“挑战”是“向那些在人类性行为方面被无情地(误导)的人传福音”。他们需要“教理讲授”和“圣事”。
范米特得知爱达荷州州长布拉德·利特尔(Brad Little)签署了该组织支持的两项法案后,得意地说:“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并不是受宗教意识形态的驱使,”范·米特在接受采访时说。“在疲惫的时候,我确实把它当作一个电池组,告诉自己不要放弃,你在这里是有原因的。”
法院很少限制谁可以作为专家证人,只要他们的证词是相关的和合理的。要求推翻反跨性别法的团体很少挑战这些专家作证的能力,因此门槛很低。但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法院在大约一半的案件中都不认可他们的证词。
欣克尔法官在否决佛罗里达州的医疗补助禁令时写道:“赫鲁兹回避和回避问题,一般来说,他作证时是一个带有深刻偏见的倡导者,而不是一个分享相关循证信息和观点的专家。”另一名法官称他的证词是“阴谋论”。
莱文的部分证词遭到了几次打击,包括依靠捏造的轶事。
在法庭上的某些时刻,辩方明显缺乏资格。最近从乔治城大学临床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的职位上退休的g·凯文·多诺万(G. Kevin Donovan)在为佛罗里达州的医疗补助禁令辩护的证词中声称,大多数变性女孩最终“恢复了自我认知”。但当被追问他的消息来源时,他却哑口无言。
记录显示,佛罗里达州卫生保健管理局向多诺万支付了34650美元。他没有回答有关他的证词的问题。
另一方也有自己的专家。通常,他们是为数百名跨性别者提供性别确认护理的临床医生,或者发表了大量关于性别确认护理的研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辩方的专家证人缺乏同样广泛的经验,通常会试图在支持性别肯定护理的研究中找出漏洞,主要是通过挑剔和歪曲证据,或者忽略较新的研究而支持过时的研究。“他们的操作方式是看着每一项研究,说它有局限性,因为它有局限性,所以完全无视它,”拉姆达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冈萨雷斯-帕甘说。“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找无视研究的理由,所以证据的数量永远不会增加。”
许多人抓住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长期的随机对照试验来测试青春期阻滞剂和激素疗法治疗性别焦虑症的效果。
将随机试验作为唯一有效的证据形式,使他们忽略了大量支持性别肯定护理的观察和临床数据。近20项随机试验组成部分的研究——对长期接受性别肯定护理的跨性别青少年进行跟踪调查,或对接受性别肯定护理的跨性别者与未接受性别肯定护理的跨性别者的结果进行比较——将性别肯定护理与更好的心理健康结果联系起来,比如抑郁、焦虑或自杀念头的减少。
这些积极的联系使得长期进行随机试验是不道德的,尤其是涉及青少年的试验。“你不会随机分配人们每天抽一包烟,”石溪大学(Stony Brook University)的研究心理学家布里安娜·拉斯特(Briana Last)说。她补充说,许多常见的医疗实践都是在没有随机试验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在过去的几周里,研究人员发表了一项针对64名跨性别成年人的随机试验,结果显示,立即接受治疗的参与者的自杀率下降了一半以上。
辩方的专家证人不会忽视研究结果,他们经常歪曲事实。许多人,尤其是莱文,指出2011年瑞典的一项研究发现,做过性别确认手术的变性人的自杀率仍然比一般人高19.1%,认为变性护理可能有害。
但该研究的主要作者塞西莉亚·德涅(Cecilia Dhejne)表示,这是对该研究的公然歪曲,该研究实际上表明,如果不打击社会歧视,仅提供医疗服务是不够的。
2022年,当拉姆达律师查尔斯罢免莱文时,他大声朗读了德涅对莱文滥用研究成果的批评。莱文没有被吓倒,今年他再次引用德珍妮的话来支持佛罗里达州的医疗补助禁令。
其中一些专家认为,其他国家,如英国、芬兰、挪威和瑞典,已经严格限制青少年使用青春期阻滞剂和激素治疗。“他们认为,总的来说,这是实验性的,弊大于利,他们正在停止,”曾在三起案件中作证的克里斯托弗·卡利贝(christopher Kaliebe)在接受采访时说。
但实际上,这些国家都没有实施彻底的禁令。在英国,国民健康服务将青春期阻滞剂的未来使用限制在一项研究中登记的青少年,青春期阻滞剂和激素疗法仍然可以通过私人护理获得。在芬兰,符合某些标准的跨性别青少年可以在该国两家主要的研究医院接受青春期阻滞剂和激素治疗。关于挪威禁止性别确认护理的报道完全是虚假的,并由以传播错误信息而闻名的网站传播。瑞典医学委员会敦促临床医生“谨慎”使用青春期阻滞剂和青少年激素,但没有要求禁止,专业提供者继续提供治疗。
性别确认护理提供者承认,他们的领域面临着悬而未决的问题,人们对自己性别认同的理解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
在青春期之前,福斯特指出,性别确认护理主要包括支持孩子,如果他们想要穿不同的衣服或剪不同的头发,或者用一个新名字。“绝大多数人会说,这就是我需要的,这就是我想要的,”她说,但“如果你的性别更不稳定,那么改变你的想法是可以的,改变你的计划也是可以的。”
她认为,性别肯定护理的反对者并不是一心要研究和改善护理,而是要根除这种护理。最近,前雇员杰米·里德(Jamie Reed)指责华盛顿大学的性别诊所急于让青少年服用青春期阻滞剂和激素。虽然她的核心主张似乎被证明是错误的或危言耸听——一位家长说里德“歪曲”了她孩子的病史;在诊所寻求治疗的近1200名患者中,里德声称有16名变性人——诊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似乎是压倒性的需求。密苏里州的回应并不是增加对青少年变性人护理的资金,而是通过了一项禁令。
“我没有看到这些人说,‘这是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让我们把资金从白人男性心血管研究转移到性别护理,’”福斯特说。“他们提出这些论点是为了支持禁令。”
在所有被要求证明雇用这些专家的合理性的政府部门中,只有起草该州医疗补助禁令的佛罗里达州卫生保健管理局(Florida Agency for Health Care Administration)做出了回应。
该机构的发言人贝利·史密斯(Bailey Smith)说:“我们的程序是透明的,基于我们向全世界展示的事实证据。”他提供了一个网页的超链接,其中包含来自赫鲁兹、莱德劳、莱文、范·米特、拉珀特等人的专家报告。“也许你只是害怕证据会挑战你对世界的偏见。”
反跨性别立法的激增意味着各州需要更多的专家来捍卫它。为了扩大法官席位,各州已经开始招募非医疗保健领域的学者,或者主要不研究人类的学者。
其中一位是曼彻斯特大学教授艾玛·希尔顿(Emma Hilton),她主要研究一种特殊的青蛙,以及它如何为理解人类遗传疾病提供帮助。
希尔顿是英国一个名为“性问题”的组织的创始人,该组织倡导按性别在法律上隔离空间。去年,她为犹他州和印第安纳州禁止变性女孩参加女子运动队的禁令辩护,每小时挣300美元。为了解释她为什么有资格参与学校的体育活动,她在法庭上说:“我热衷于业余运动,业余爱好是打无板篮球。”
“我们对人类生物学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动物模型研究的结果,”希尔顿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她拒绝谈论无挡板篮球的相关性,它就像没有运球的篮球。
另一位是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迈克尔?比格斯(Michael Biggs),他在法庭上承认,曾在笔名@MrHenryWimbush下写过厌恶变性者的推文,并称自己是一名“少年混混(变身)牛津大学教授”。一个有代表性的帖子写道:“变性恐惧症是法西斯主义者创造的一个词,被懦夫用来操纵白痴。”
佛罗里达州每小时支付比格斯400美元,为其医疗补助禁令辩护。但他在专家神殿中扮演着另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大量发表质疑性别确认护理效果的出版物。他经常引用的对青春期阻断激素的批评之一,是基于对绵羊激素试验的可疑解读,在这些试验中,绵羊似乎有焦虑。其他专家也多次引用比格斯的观点。

挑战阿肯色州性别肯定护理禁令的少年迪伦,不愿考虑这些人的论点占上风的未来。相反,他考虑去一个没有敌意的州上大学,学习教育。他说:“我遭遇过很多欺凌,但我遇到了一些非常棒的老师,他们给了我一个安全的地方。”“我想为别人成为那样的人。”
他的诉讼已经为其他跨性别青少年提供了一个临时庇护所。今年6月,一名法官推翻了阿肯色州的禁令。该州召集了一批专家——拉珀特、赫鲁兹、莱文和雷格纳斯——但用美国地区法官詹姆斯·m·穆迪的话来说,“未能证明对患有性别焦虑症的未成年人的性别确认护理比向未成年人提供的其他医疗护理无效或风险更大”。
“他比这些人都更清楚自己是谁,比我更清楚,他们都没有权利对他说不一样的话,”乔安娜谈到儿子时说。
迪伦说:“当我开始服用睾酮时,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可以正常呼吸了。”“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已经能够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微笑。它在很多方面改变了我的生活,拯救了我的生活。”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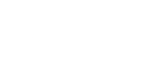
发表评论